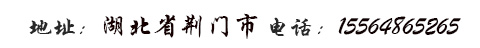学各家学说,别被特色蒙了眼
|
中医书友会第期 每天一期,陪伴中医人成长 作者/张英栋 I导读:在学习历代医家的理论时,中医学子很容易被其流派所迷惑,攻邪派是否只攻不补?寒凉派是否只用凉药?为了打破这种无意中形成的误区,本文作者提出,面对各家学说,“看到偏,我们是要区别各家的不同;看到不偏,我们才能看到古圣先贤真实的高度。”细思,很对。 无执故无失(3)——“名家”皆不偏 古代医家能经历漫长的岁月,流传至今的能有几人?《中医各家学说》教科书中的历代医家,是经历了怎样的偶然和必然,才有资格展现在当代人眼前的呢? 学习中,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。 于是当有研究各家学说的学者对我说,“中医各家学说”应该叫做“中医名家学说”的时候,我欣然认同。这位学者还告诉了我另一个观点:“研究各家、研究流派,不仅要看其不同,更要寻找其相同点。”这个观点也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——通往古代医家、中医各个流派核心观点的窗户。 认识问题需要智慧,有的时候,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,就可以点亮我们认识问题的智慧,帮助我们换个角度,更接近历史和现实的真实。我非常感谢这位学者,经由他的指点,我看到了我之前没有看清的真实。 看到偏,我们学习的是各家;看到不偏,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名家。 看到偏,我们是要区别各家的不同;看到不偏,我们才能看到古圣先贤的高度。 本文将以偏与不偏这个视角,来试着还原古之大家的思维之一斑,希望对于今天的中医同道成才会有所助益。 先来谈不偏
中医学术史上有一种说法,医之流派起源于金元。金元四大家,其理论多为纠偏而作,过正才可矫枉,所以从理论来看他们却好像是偏的。但实际上,其实践并不偏: 刘河间立论主寒凉。而实践中“对附子、干姜之类的温热药物不是拒绝使用的。后世有人对他的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中记载的首处方进行了统计、分析,发现其中使用寒凉药物的比例只占到1/6左右,而对附子、官桂、细辛、肉豆蔻等温热药的使用却为数众多,且颇具心得。” 张子和立论主攻邪。而实践中“并不反对正确进补。他说:‘凡病人虚劳,多日无力,别无热证,宜补之。”在《儒门事亲》卷十二的首处方中,具有进补功能的处方计51首,占内服处方总数的1/3;在卷十五的首处方中,具有进补功能的处方计58首,占内服处方总数的1/3强。他还搜集、总结、创造出大量的食补处方,如生藕汁治消渴、粳米粥断痢、冰蜜水止脏毒下血、猪蹄汤通乳等。 李东垣立论主补土。而实践中“在脏腑标本、寒热虚实的辨证中……创造出许多对后世影响重大的祛邪良方。在他的著作中,治疗湿热下注的凉血地黄汤、治疗咽喉肿痛的桔梗汤、治疗心胸热郁的黄连清膈丸等,显然都不是以补脾为主的。在他的学说中,补与清、补与消、补与下不是绝对对立的,而是在‘和’的基础上彼中含我、我中有你……” 朱丹溪立论主滋阴。而实践中“从未废弃对温热药物的辨证应用。他主张以气、血、痰、郁、火论治,辨虚实顺逆,寒热往复,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攻、补两大学说的精华。在《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·朱丹溪医案》一书所治之病的案中,涉及的处方为54则,药物94味,其中寒凉药物的比例是有限的,而热、温成分的药物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。”(以上引文均出自温长路《我说中医》一书) 每一个医家都会在《内经》中吸取营养,但其观点多不同、甚至相反;原因是《内经》作为一部论文集,其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。理论的争辩围绕实际的话,可以使临证方向更明确,也可以使学问做得更严谨、视野更开阔。但理论的争辩脱离临床实践的话,就会流于空泛而显得苍白。 中医学对人体长寿以及衰老的论述极为丰富,如:《黄帝内经》的肾精、气血说;《华氏中藏经》的阳气衰惫说;《千金翼方》的心力减退说;《养老奉亲书》的脾胃虚弱说;《寿亲养老新书》的气滞而馁说;《徐氏医书八种》的元气不足、阴虚生火说等等。均未能脱离“虚损”之范畴。当代国医大师颜德馨结合50年的临床实践,年初提出“人体衰老的本质在于气虚血瘀”新学说(见于《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·颜德馨》一书)。颜德馨衰老理论别具一格,他是在临证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,如果囿于既有的理论,只在故纸堆里找依据,怕是难有这样理论上的突破的。 在为高建忠的《临证传心与诊余静思》一书所作的跋中,笔者曾写下这样一段话“……攻击是否在一个适当的位置?如果有所偏,应该及时调整,此所谓‘攻击宜详审,正气须保护’之意。有病就是身体偏了,没有矫枉过正的过程,就不会有复正的结果,但是纠偏可以,一定要明白你的最终目的是中,而不是过,所谓“执中以纠偏”是也……对于每个人治疗风格的形成:我认为不当有褒贬之主观先见。李东垣临证如此,张子和临证如彼,是因为所面对的患者不同……‘一类患者一类医’,在不断的磨合中,大浪淘沙,医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这种风格会吸引、吸纳一类患者,这些患者又反过来强化了医者的风格,但同时却在滤掉另一类患者……想成为大医者,必须有更宽的胸襟、更高的视角。” 争辩是可以的,但争辩的双方一定要对于各自观点的差异做客观的分析。争论的各方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偏的,切勿将在自己的患者群中得到的部分真理夸大成绝对真理,这样就可以对于别人的观点更加宽容。同时要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偏,临证中执“中”以纠偏,在适合于自身之偏的患者群中要积极地发扬这种偏,让疗效向极致攀登;在不适合自身之偏的患者群中,要勇于承认自身之短,在别人的观点中寻找有益的启示,不断地减少自身的临证盲点。 要宽容地对待不同的观点,这样才可以保持思维的宽度,在临证中面对疑难病时才可以有更多的思路;要尽量提升思维的高度,让不同的观点在新的高度上各自安于适当的位置,而不必互相攻讦。 从更高的层面来观察,各家的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。其差异源于各自的实践的局限,和观察的角度不同。更高的层面可以让不同的角度一览无余,这样各家的观点就有了统一的可能。 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用于学术进步的描述上是很恰当的,不断地面对“一山过后一山拦”的困惑,不断地进行“更上一层楼”式的攀登,当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回望时,你会发现所有的不同,所有的争辩都会以“众山小”的姿态各安其位。 再来说偏 王好古《此事难知?卷下》有一段很精彩的话:近世论医,有主河间刘氏者,有主易水张氏者。盖张氏用药,依准四时阴阳升降,而增损之,正《内经》四气调神之义,医而不知此,是妄行也。刘氏用药,务在推陈出新,不使少有怫郁,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,医而不知此,是无术也。然而主张氏者,或未尽张氏之妙,则瞑眩之药,终不敢投,至失机后时而不救者多矣。主刘氏者未悉刘氏之蕴则劫效目前,阴损正气,遗祸于后日者多矣。能用二家之长,而无二家之弊,则治法其庶几乎。 作为易水学派的传人,王好古给我们留下这段平心之论,说明他有不偏的追求。 但是他偏不偏呢? 在那段话里,首先他看到了两位大家在后学者那里可能出现的偏——主张氏者,未尽张氏之妙,则瞑眩之药,终不敢投,至失机后时而不救者多矣。主刘氏者,未悉刘氏之蕴,则劫效目前,明损正气,遗祸于后日者多矣。 王氏看到了两位先辈可能被误读的倾向,于是提醒大家,如果能不偏,则学习张元素能尽张氏之妙,则瞑眩之药也是敢投的,这样可以抓住治疗疾病的有利时机,积极地治病;而学习刘河间能学到精髓,就不会劫效目前,阴损正气,越学得深入越会注意人体正气,最终的效果要靠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ihuisuana.com/hhsyf/1041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倪海厦糖尿病的成因与真相国人必读转发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