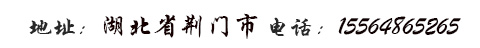附子治疫病谈圣散子也治年己庚之疫
|
附子治疫,几乎所有中医人都不相信吧?他们以为治疗瘟疫,无非清热解毒、滋阴添精、活血化瘀而已吧? 《素问·本病论》《刺法论》中提到的瘟疫,分为疫疠两种。司天失政为疫,司地失政为疠。五行五运感应五脏,每一脏都有疫疠之分。也就是说,金木水火土,温热寒凉燥湿都可以致疫。何况仲景家族亡于伤寒者十有七八。可见寒疫何其猖獗! 不但仲景书中的经方可以治疗寒疫,后世也有许多治疗寒疫之方。如圣散子方便是其一。所谓“圣散子方”,是北宋大文豪苏轼所传,并经他大力提倡,在宋明两代都很流行,还有刊本流传。 《东坡全集》卷三十四收有《圣散子方叙》和《圣散子方后叙》两篇文章。《圣散子方叙》说明了“圣散子方”来龙去脉:“今仆所蓄圣散子……其方不知所从出,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。谷多学好方,秘惜此方,不传其子,余苦求得之。谪居黄州,比年时疫,合此药散之,所活不可胜数。巢初授余,约不传人,指江水为盟,余窃隘之,乃以传薪水人庞君安时。安时以善医闻于世,又善著书,欲以传后,故以受之,欲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。”《圣散子方后叙》则叙述了疫病流行时,使用此药的效果:“圣散子主疾,功效非一。去年春,杭之民病,得此药全活者,不可胜数。”由此可知,苏轼从眉山巢谷处获得“圣散子方”,并将其传授给了好友、名医庞安时,希望借助庞的著作使该方传世。 两宋疫病流行的危害程度及发病频率和隋唐五代时期近似,据《三千年疫情》统计,北宋的疫病流行有22次,南宋有29次。庞安时(-),著有《伤寒总病论》,苏轼的《圣散子方序》及“圣散子方”均被收于其卷四“时行寒疫治法”条下。据黄庭坚撰《伤寒总病论序》,该书成于元符三年(),故可认定这是医方书中关于“圣散子方”的最早记录。 苏东坡在关于“圣散子方”的介绍文字里公开写道“昔尝见《千金方》三建散,于病无所不治。孙思邈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。至于救急,其验特异。乃知神物效灵,不构常制,至理开感,智不能知。今余所得圣散子,殆此意也欲。自主论病,惟伤寒至危急,表里虚实,日数证候,汗下之法,差之毫厘,辄至不救。而用圣散子者,不问阴阳二感,状至危笃者,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,饮食渐进,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。其轻者,心额微汗,正尔无恙,药性小热而阳毒发斑之类,入口即觉清凉,此不可以常理诘也。时疫流行,平旦辄煮一釜,不问老少,各饮一大盏,则时气不入其门。平居无病,空腹一服则百疾不生。真济世之宝也。其方不知所从出,而故人巢君谷,世宝之,以治此疾,百不失一,既得之。谪居黄州,连岁大疫,所全活者不可胜数。巢甚秘之,此方指松江水为誓盟,不得传人。予窃隘之,以传蕲水庞君安时。庞以医闻于世,又善著书,故以授之,且使巢君名与此方同不朽也。” 圣散子。据宋刻本载,其方药有高良姜(麻油拌炒)、白术(去芦)、白芍(去皮)、藁本(去皮)、茯苓(去皮)、柴胡(去芦)、麻黄(去根节)、防风(去芦)、泽泻(去皮须)、猪苓(去皮)、藿香(去枝土)、细辛(去苗)、吴茱萸(汤洗七次)、独活(去芦)、苍术(去黑皮,米泪一水浸)、枳壳(去皮,麸炒)、厚朴(去粗皮,姜汁制,炙)、半夏(汤洗七次,姜汁制)、附子(炒制,去皮脐尖)、石菖蒲(忌犯铁器)以上各半两、甘草(炙,一两)、草豆蔻(十个,去皮)等22味,用以“治伤寒时一行疫病、风温、湿温,一切不问,阴阳两感,表里未辨,或外热内寒,或内热外寒,头项腰脊拘急疼痛,发热恶寒,肢节疼重,呕逆,喘咳,鼻塞声重及食饮生冷伤在胃,胸隔满闷,伤肋胁胀痛,心下结痞,手足逆冷,肠鸣泄泻,水谷不消,时自汗出,小便不利,并宜服之”。 年苏东坡结束第一次流放后复官,不久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外放杭州。年(己巳,其运气格局同于己亥)春天到达杭州(又是五宫之地),恰逢南方大旱后疾疫流行。苏轼即以圣散子方为主药进行治,其治疗效果一如他在第二年所写的《圣散子启》中所说,“全活不可胜数。”由于当时疫情特别严重,苏东坡还发动民间捐款支援抗灾,自己以身作则,捐出黄金五十两,加上集资,创办了一所病坊,名为“安乐坊”,收纳贫苦病人,这是我国历医院,是公私集资的传染病院。苏轼在这篇以个人兼杭州官方名义公布的启事中写道:“圣散子主疾,功效非一。去年春,杭州民病,得此药,全活不可胜数。所用皆中下品药。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,所济已及千人。……自立春后起,施至来年春夏之交。有入名者,径以施送本院。”这更加使圣散子之名天下皆知,甚至有人刻石为铭将其方记录下来。 凡事讲究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此一时,彼一时,无论从大司天、流年司天,及日司天上都是不同的效果。运气格局的不同,就会导致不同的治疗效果,甚至是负面效果。 最近比较流行的《三因司天方》,即是出于陈言,字无择,号鹤溪道人,浙江青田人,为南宋永嘉医派创始人。其著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,为诫后人慎之,将苏翁之序全文录下,并于“圣散子方”后特加评语:“此药以治寒疫,因东坡作序,天下通行。辛未年(年),永嘉瘟疫,被害者不可胜数,往往顷时。寒疫流行,其药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,未可考也。东坡便谓与三建散同类,一切不向问,似太不近人情。夫寒疫,亦能自发狂。盖阴能发躁,阳能发厥,物极则反,理之常然,不可不知。今录以备疗寒疫用者,宜审之。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。” 陈无择首次提出了圣散子治疗寒疫的观点,并强调在疫病的诊治中“不可不究其寒、温二疫也”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成书于年,距离“辛未年”()仅20徐年,作者对当时“圣散子方”流行的情况应是相当了解的。 尽管南宋时已批评过滥用“圣散子方”之弊端,但到了明代又忘记了先前的教训,“圣散子方”再度流行,明·俞弃的《续医说》云:“圣散子方,因东坡先生作序,由是天下神之。宋末辛未年,永嘉瘟疫,服此方被害者,不可胜计。”“弘治癸丑年,吴中疫病大作。吴邑令孙磐,令医人修合圣散子,遍施街衢,并以其方刊行。病者服之,十无一生,率皆狂躁昏瞀而卒。隐孙公之意,本以活人,殊不知圣散子方有附子、良姜、吴茱萸、麻黄、藿香等剂,皆性味燥热,反助火邪,不死何待。若不辨阴阳二证,一概施治,杀人利于刀剑。有能广此说,以告人人,亦仁者之一端也。” 什么叫好心办坏事,什么叫后悔不迭,当时的孙磬是最清楚的了。这不是圣散子之误,不是麻黄、附子、细辛之误,乃应用圣散子不当之误,乃是应用麻黄、附子、细辛之误。以一方统治百病而“一切不问”,不察地气、不明天气、不辩人气,能不偾事者几希! 明·张凤逵在《增订叶评伤暑全书》一书,明确地指出:“疫多病于金水不敛之年,圣散子寒疫挟湿之方而设,永嘉、宣和年间服此方陨命者,是因为以寒疫之方,误施于温疫而致。”清代伤寒医家尤怡也认识到因为运气环境不同,疫病有表、里、寒、温、热、湿之分,不可一概而论,并明确指出苏东坡圣散子之证,是属“寒湿”之疫,强调“法不可不备,惟用之者得其当耳”。温病学家吴鞠通,也指出了寒疫与温病的不同,并揭示出了寒疫与运气的关系,认为“六气寒水司天在泉,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,或六气加临之客气为寒水”,是寒疫发生的运气环境。 王朴庄运用大司天理论,对“圣散子方”在宋代治疗疫病前后迥异的效果做了分析,认为自黄帝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司天,后三十年少阳相火在泉开始,至苏东坡以圣散子治疫时,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太阴湿土在泉,而至辛未年时己交六十四甲子,相火已经开始用事。运气环境变了,而仍以温燥的“圣散子”治疫,难免会有贻误。陆懋修承其外曾祖王氏之学,对“六气大司天”做了进一步的发展,在其著作《文十六卷·卷六·附:瘟疫病选方》中,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:“公谪居黄州,尚在六十三甲子,湿土运中,方必大效。至五十岁后,又值六十四甲子,相火之运,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。” 此六人之言,可谓切中肯綮,发人深省。不是麻黄、附子、细辛不能治疗疫病,是不能治温疫,但是可以治疗寒疫。不识天地人之气,无异于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。施治于药,也无非五苦六辛之烂。历历医事,明明在目,选择性失明者,竟然如过江之鲫多。不是故意为之,就是学识枉然。 附子治疗疫病,历来相传不断。 日本人源元凯依《岭南卫生方》悟出天明戊申()年之表热里寒证。天明戊申年,为西元年,而自年至年,大司天为太阴湿土司天,太阳寒水在泉。年正属大司地之寒水之气。申年为少阳相火对化火不及之年,火不及则水克之,一片汪汪寒水之气。证同冷瘴,故用真武汤、茯苓四逆汤,或四逆、附子理中汤而治此疫证。甚至“邪传于胃,大热短气,心下鞕急其脉数疾如急湍。欲攻胃,则有害于肾;欲回下虚,反助上实”之证,也用真武汤,去术加甘草愈之,其为少阴太阳与太阴之证明矣。此病,时医尚依吴又可的《温疫论》投以柴胡辈,结果“延捱引日,遂至于危殆。”最后因为读《岭南卫生方》而悟得此表热实寒之证。 若天地之间无有五运六气以化生三阴三阳之病一事,则吴又可的达原饮既可愈崇祯辛巳之疫气,则当可以此方治愈天明戊申之疫病,何以前后用药如此之悬殊?若气运有变,阴阳必异病,则不明五运六气,达原饮自不能尽愈今后所有的疫病,此理甚明。同理,可知源元凯所遇之疫,与《岭南卫生方》所治之病不相涉。《岭南卫生方》所治之冷瘴,自有其运气加临的关系,源元凯所治愈之戊申之疫,宜为寒湿司天在泉所感生的太阳少阴与太阴三感之证。此事足可破《伤寒论》方只能治伤寒,不能治温病之疑;也可破《伤寒论》不能治疫病之迷。人之不能用《伤寒论》方法治疫病者,实不明五运六气与《伤寒论》之关系之故,致无法登仲景之门,探其骧实而已。 清·邵登赢于清嘉庆二十年乙亥(年)所著之《温毒病论》一书而言:邵氏自述曾治乾隆丙子君相司令之际(年、乾隆21年)的大疫。当时疫情:“沿门阖境,死者以累万计。”对于此症,邵氏云:“此疫邪直犯包络,入脏之症。清之、开之、攻之,终不免于死。”“如胸背周身稠密如织,其毒必重,屡斑发天毫缝者,即勉投黑膏、紫雪、金汁,人中黄等,如水投石、热反炽、神渐蒙,口秽杂近,营卫不行而死矣。又有日夜烦躁,斑见陷处色青紫,而腰以上反远进,此毒陷三阴,必死之证。”“予见病温之人,右脉搏大,愈按愈劲,不为指挠,狂烦大热如火,口秽喷人;欲得水饮,未尝不白虎清之,承气下之。然药自药,病自病,不减分毫而死,何也?”所以邵氏“勉以陶氏黄龙汤下之,十中亦救一、二。” 对于此证,医家见其大热神昏、烦躁、口渴,以为是燥症、火症,而不知阴症有格阳之热症,有烦躁之逆症,故虽见其毒陷三阴,仍不敢用热药。其实并非一见大热、神昏、烦躁、口渴,即可认定是火燥之症。犹之王海藏所治宝丰阿磨堆候君辅之学丞,虽见斑出、狂乱,由于身处寒水司天,故用姜附二十余两而愈。 此症发于年,而自年至年为太阴湿土司天,太阳寒水在泉。丙子年,丙为水运太过,子为少阴君火对化不足,寒水来克。可知天地一片寒湿。虽然子年君火与主客气相火生湿土,反见燥化,终究寒湿为重,所以清之、攻之、开之,终不免于死。若能有一医者,于大热烦渴之中,识破寒湿之真气,必可如源元凯一般,用附子、干姜愈此重疫。 近人以附子治疫也有传灯者。 翟冷仙(-),江苏省东台市人,平生勤勉好学,行医60载,学验俱丰,而于仲景之学造诣尤深,在临床和理论研究方面成绩显著。他运用大青龙汤加附子治疗“乙脑”、“流脑”及其后遗症的经验就是附子治疫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于某,男,10岁。因发热、头痛,继而昏迷、抽搐1天,于(甲寅)年7月24日初诊。体温38.90C,经脑脊液等检查诊断为“乙脑”。证见头痛项强,壮热无汗,口渴烦躁,两目上视,痉挛抽搐,神识昏迷,四末微厥,大便秘结,小溲自遗,口虽不噤但舌卷不能言,脉浮数。翟氏诊为“太阳少阴两感于寒”之温病,予大青龙汤加附子治之。药用:麻黄(去节,先煎去沫)、光杏仁、熟附片各lOg,桂枝、炙甘草各6g,生石膏(碎)60g,红枣6枚,鲜生姜3片。每日1剂水煎服,每隔3小时服1次。服2剂后已得汗出,体温降至37.80C,神志稍清,舌卷已伸,抽搐亦减,连服6剂,诸症消退。 “乙脑”为急性热病,属中医“暑温”范畴,临床一般以卫、气、营、血辨治,而翟氏从六经辨治获效。所谓“两感证”,即太阳与少阴俱病。《伤寒论》曰:“若感于寒者,一日太阳受之,即与少阴俱病,则头痛口干,烦满而渴。”翟氏认为,年处于第78甲子,太阳寒水大司天,太阴湿土大司地。病者头痛项强、壮热无汗、脉浮,为感天地之寒邪,伤及太阳之表,致玄府闭塞,卫气不得发越;烦躁、口渴、脉数,乃表邪化热内传;肢厥为寒伤少阴之象。概言之,乃太少合病,故治以大青龙汤解表清里,加附子温经散寒,俾汗出、热退、寒祛而病除。 20世纪50年代,华北地区“乙脑”流行,石家庄地区采用了名医葛可民的处方,按“暑温”治疗,取得了满意的疗效。次年北京地区又流行“乙脑”,再采用此方却不灵验了,疫情难以控制。蒲辅周率领中医研究医院等,采取了辨证施治的方法,力挽狂澜,扑灭了疫情。同样是“乙脑”,治法却不同。这在非医学专业的人是难以理解的,在西医也同样是难以理解的。这一点只能让西医与中医来接轨,不可能中医和西医接轨。 年末,年初,己庚之寒湿疫,蝙蝠、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只是纳米级病毒的媒介,运气不到,任你上蹿下跳也不会发病。运气密码一对,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。五宫之地,下燥湿、上风寒,一片寒湿之气弥漫,大小青龙汤加附子主之,五苓散亦主之,圣散子亦主之。后来的治疫协定处方也印证了这一预测。不仅官方,民间中医更是有用附子、麻黄、细辛等治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量病案。如果李医生用了中医中药,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幺蛾子了。 哪有附子不能治疫的说法,都是外行话。 若不识运气,读破万卷,亦无识真经理趣何在?抄尽方药又怎知何方可愈此病?则一部医学史也只不过是一本糊涂帐而已。 金元间,疫情出现,不少医家以伤寒之方治疗,百无疗效,但后来出现了寒凉学派。乾隆癸丑()春夏间,京中多疫,以张景岳法治之,十死八九,以吴又可法治之,亦不甚验,后来出现了善用石膏的余霖。SRAS的流行已经为我们上了一课,三年化疫说也就此传开。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又乘着天地之戾气汹涌而来,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,我们为什么不射擒新型冠状病毒所承的这匹马——寒湿之天地气呢? 此事难知,此事便是天地之间事。 识得天地气,煮得人间味,皆是珍馐美馔。 无极之镜随缘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ihuisuana.com/hhsxf/1040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金匮腹满,腹中寒气,心下满痛,胆囊胆管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